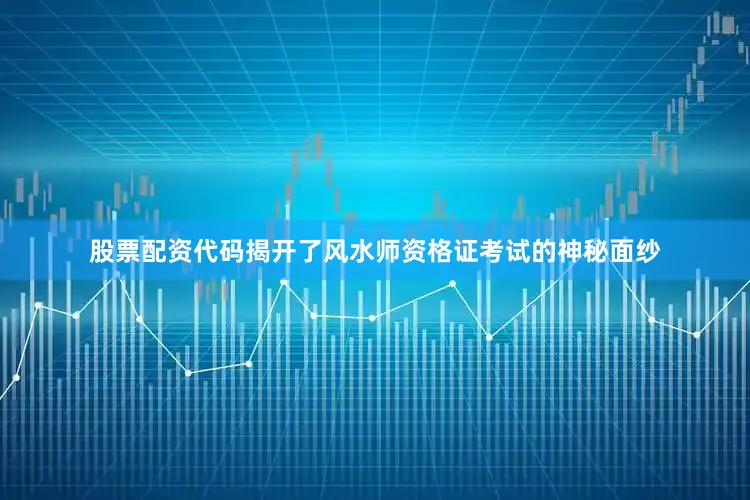1939年的上海“孤岛”,在如此群敌环伺的恶劣环境中,“意志不坚定者更将趋向歧途”,意志坚定者如郑振铎,也不免陷入了“精神内耗”。

1939年1月,郑振铎在《华美》周刊上发表散文《在腐烂着的人们》,如此刻画因对抗战前途丧失希望而沉沦腐烂的人们:
在腐烂着的人们无目的地在漫游着;他们对于自己没有信任,对于朋友没有信任,对于国家的前途没有信任;他们自己觉得在黑漆漆的长夜漫游着。这漫漫长夜,他们觉得永远不会变为灿烂光明的白昼。……
在腐烂着的人们一窝蜂的在那些腐烂的百货商店,旅舍,戏馆以及酒馆里进进出出。从酒馆里出来的是红红的脸,带着微醺,一支牙签还斜衔在嘴角。给晚上的西北风一吹,更显得酒力的微妙作用;觉得这便是抗抵,这便是争斗。[1]
文章中还说,在腐烂着的人们相信着突现的奇迹。以此,他们相信神道、星相、命运,热衷于看相算命,委身待运。
这篇文章,其实也是郑振铎写给自己的警醒。此年他与妻子高君箴一起沉溺于打麻将,日记中称为“雀戏”“雀战”。
3月19日,在寓晚餐,餐后雀戏至二时许才散,输了近二十元。他在日记中自责:“此种劳民伤财之戏,渐宜戒止也!”
3月28日,郑振铎与徐调孚、周予同到王伯祥家祝贺“伯翁”五十大寿。寿宴后,大家赌了一场,郑振铎负二十余元。第二天与太太同到暨大同事张耀祥家中雀战,至深夜一时许始回,胜约三十余元。
4月5日下午三时,同到张宅雀戏。至夜十一时半许散,负三十余元,“精神已经很疲倦了”。雀战得胜的最高纪录是10月15日,赢了八十余元;输的最高纪录是8月20日的六十余元,这天他再一次发誓不打——“戏无益!”
8月29日,仍在张宅雀戏,胜五十元,还了账上的旧欠。“尚有许多事未做,而耽搁了下来,去从事无益之戏弄。”

9月1日,又是熬夜雀战,又是自责:“有无数的事要做,但都放下了,却去做这不急之务。到底是好整以暇呢?还是糊涂?亟应自省。”
孤岛上的文化人,处于民族家国的道德理想与日常生活压力的紧张拉扯之中,这种张力带来了无时无刻的焦灼与疲倦。越是疲倦,越是逃向“雀戏”;游戏胜负立见的刺激一方面舒缓了焦虑,散场之后,又加重了玩物丧志的负罪感。
《译报》主笔胡仲持的女儿回忆其父在孤岛“低气压”中的高度精神紧张——
物价飞涨而我们家人口又多,加之父亲周围一些没有职业的亲友,经常在我家吃饭,几乎每天开饭两桌。沉重的生活担子,复杂的斗争形势,使我父亲每天睡眠极少,而神经又极度紧张,但仍不停止写作,直至昏厥到神志不清,甚至一反常态,跺着脚高喊: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,跪在《鲁迅全集》的书箱前痛哭。在这样的时候,又是地下党的朋友们的深情关怀,给他以帮助。王任叔等同志像哄孩子一样,教他打牌,做游戏,故意让这个从来不会打牌的人取胜,以放松思想,解除烦恼。[2]

上半年,郑振铎的学术写作陷入停滞状态,他在日记中不断地给自己打气——
2月25日,预备写文一篇,但始终写不出来。
4月30日,整理书箱及写目录。“惜一分阴!”
5月26日,每天胡里胡涂的过去,要写的东西始终没有动笔,不知如何是好。
5月27日,雀战至十一时半,散,计负六十五元,为年来负得最多的一次。精神颇不愉快!明天一定要动手工作了!至少有一个月以上不曾动过笔墨,似乎过于懒惰与不振作了!应努力,惜寸阴!
6月15日,在家写《风涛》[3],好久不曾动笔,觉得很吃力!
7月2日,心里和天色一样的阴晦。有许多事要做,却一件也不曾做。
7月30日,不知怎样的,有些无端的悽楚。
12月17日,今日是四十三岁的生辰。正是壮年努力之期,至少应每半年出书一种。
在这样的心境中,郑振铎还是在年底交出了两篇学术研究文章,一篇是近两万字的《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[4],一篇是近三万字的《劫中得书记》(包括一篇长序和八十九则古籍版本提要)[5]。二文皆在他主编的《文学集林》上发表。
此年11月,郑振铎与开明书店的徐调孚创办了《文学集林》,广邀巴金、叶圣陶、丰子恺、李健吾、柯灵、耿济之等名家撰稿,可以说是“孤岛”上最负盛誉的综合型刊物。

郑振铎主编的《文学集林》第一辑,封面左下照片是随政府内迁、此年不幸病逝于云南大姚县的曲学大家吴梅。本期刊发一篇纪念吴梅的文章。
截至1941年6月,《文学集林》共出五辑,由开明书店总经售,除了上海版,刊物并在桂林分店依照上海纸型重印,销量甚佳。抗战时期上海的文艺刊物在大后方同时重印发行的,似乎只此一家。
郑振铎在每辑《文学集林》上都有文章发表,徐调孚说:“郑先生从内地接下这个任务来托我编的。编到第五期,钱完了,就停刊了。”[6]
《文学集林》每辑采用不同的刊名,以书的单行本方式发行,这样就避免了向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登记。万一被查禁没收,牵连不广。这一谨慎做法,后来就证明了其必要性。
郑振铎12月29日记写:“闻《集林》遇劫,为之大惊!”这个时间正是《文学集林》第一辑发行之后,但他日记没有记录此事的下文,查当天报纸,《大公报》《申报》均报道:
【沪日方特务队在租界横行竟搜查协丰印刷店并绑去店主毛树钧】日本特务队员四人,二十九日晨九时许乘汽车至福煦路搜查协丰印刷店,将店主毛树钧绑入汽车,驶往沪西,并搜去该店承印之开明书局《文学集林》及新智书局《国际英文选》两书纸版。[7]

日本特务越权到租界抓捕,立即引起公众关注,租界捕房为此展开调查,发现店主毛树钧经营的印刷所承印《文学集林》等各项书籍,被怀疑其中夹有抗日书籍,致被日人绑架到宪兵总部审问关押。日本特务从《文学集林》等九十二本承印书籍中没能找出“抗日”证据,经过租界捕房和律师的交涉,于1940年1月6日释放了毛树钧[8]。
在“孤岛”上,郑振铎和他的朋友们善于与敌伪周旋,小心谨慎地维护着《鲁迅风》《文学集林》《民族公论》等多种进步刊物的编辑与运行。
“孤岛”束缚了他的自由,然而复杂的斗争环境也激发了他的战斗潜能,同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许觉民说——
孤岛的四周固然布满着豺狼,文化战线上的战士自不能失去警觉,但是租界的特殊位置,却给了孤岛的文化阵地多多少少施展的机遇。困难自然是说不尽的,一种书刊被扑杀了,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又派生了另一些新的来;某些固定名称的刊物,不时地更换着每期不同书名的丛刊,以避开捕房的追踪。我的感觉是虽然紧张一点,但是在隙缝中抢得到一点“自由”,比国民党地区那种天罗地网式的统治宽松得多。[9]
郑振铎从2月5日开始整理家中书籍,因久不开箱,有许多书都已为蟑螂作根据地了。整理藏书又燃起购书冲动,他每天到四马路及三马路各书肆一行,抑制不住诱惑,每天都会挟一两种古书回家。

5月25日自我反省:“购书之兴,迄未衰,是一大病!爱博不专,尤为不治之症!”但还是继续地买买买。
8月15日的日记又再反省——
书囊无底!因为整理,便感到不够,感到收藏的贫乏,感到有若干必要的书还未购入。不知什么时候才有满足的可能。
1939年,旧家珍藏的各朝各代善本古籍,源源不断地从长江中下游的沦陷区流散到上海,进一步推高了上海古旧书业的行情。
郑振铎日记和《劫中得书记》记录此年他在四马路各书店买到的古籍,多为常熟、杭州、苏州等地藏书家的旧藏。
比如他花五元买下的明刊《琵琶记》,原藏家的扉页识语写于二十八年前:“民国元年六月十八号,同乐之、中甫游永定门。途经琉璃厂,于旧书摊上,以铜元八枚易之。”[10]

这是时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厅卫生处处长陈万里的藏书,陈氏当时随军撤退到浙江山区,他杭州家中藏书皆被盗劫,郑振铎还买到陈万里所藏内府钞本曲数种。
上海藏书家也在出售旧藏以济困。晚清重臣李鸿章晚年寓居上海,小儿子李经迈经商有方,20世纪30年代曾建有枕流公寓、丁香花园等上海滩顶级公寓洋房,其藏书楼“望云草堂”亦富藏精善本。
李经迈于1938年去世,其子无意在沪久留,遂将藏书中的珍本卖给汉文渊书店,其余书捐给震旦大学。此批“合肥李氏书”在1939年夏天经汉文渊书店转卖给来青阁[11],5月21日,郑振铎从来青阁购得二十六种古籍,共一百三十元,当时付了二张支票,“款尚不知如何筹法也”!
接下来一星期,郑振铎沉浸于给新获古书写提要,他欣喜地发现,来青阁这批合肥李氏藏书中最为精者《佛祖统纪》《午梦堂集》,皆入自己手中。
世界书局创始人沈知方1939年9月11日病逝于上海,他的粹芬阁藏书在生前即已散出,此年7月23日,郑振铎日记载他在中国书店,“见沈氏书散出者不少,颇思得之,而苦于有心无力”。
他在《劫中得书记序》中亦记“今岁合肥李氏书、沈氏粹芬阁书散出”,限于财力,郑振铎只购得沈氏书的七八种,其余都被北平的书店网罗而去。沈氏所藏《异梦记》是罕见的善本,郑振铎略一踌躇,书已为“平贾”所攫,携之北去。
1939年,从北平南下的书商(郑振铎称之为“平贾”“平估”)明显增多,来薰阁、修绠堂、富晋书社等六家北平书店来沪设立分店。

7月25日郑振铎记:“赴中国书店等处,四顾几皆为某种人,可惊!”
9月5日,到中国书店等处,“刚到了一批书,已为平估一抢而空”。由于南北汇率的差价,再加上北平的藏书家更多、市场更大,“平贾”在上海收购江南的图籍,打包北去,得利可达三倍以上。“以是南来者益众,日搜括市上。遇好书,必攫以去。诸肆宿藏,为之一空。”[12]
郑振铎《求书日录》历数“平贾”的危害——
而他们所得售之谁何人呢?据他们的相互传说与告诉,大约十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去,以可以得善价也。偶有特殊之书,乃送到北方的诸收藏家,像傅沅叔、董绶经、周叔弢那里去。殿板书和开化纸的书则大抵皆送到伪“满洲国”去。
我觉得: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都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,将来总有一天,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。这使我异常的苦闷和愤慨!更重要的是,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收购的书,都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者为主体,其居心大不可测。近言之,则资其调查物资,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;远言之,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。[13]
原来上海尚有一批兼具财力与眼光的商人藏书家,即郑振铎所说的“有力者”,本地书店收得好书,往往先被这些沪上藏书家所截留。中国通商银行的常务董事谢光甫,“每天下午必到中国书店和来青阁去坐坐,几乎是风雨无阻。他所得到的东西似乎最多且精”[14]。

1939年6月18日,谢氏逝世,郑振铎在日记中感叹:“书友又少一人矣!”在租界工部局当大买办的潘明训,也是古书巨擘,其“宝礼堂”专藏宋元版,陆续收得一百多部宋版书。
潘氏也于此年6月去世,精刊善本失去了这些沪上“有力者”的收购拦截,就会被南下的书贾搜刮之后流向伪北平甚至海外。郑振铎在《劫中得书记》中呼吁:“安得好事且有力者出而挽救劫运于万一乎?”
失去了“有力者”盟友,郑振铎只能挖肉补疮,抵押出售自己藏书,以供拯救文献之资。
日记中记载,6月2日,他整理出二十箱书籍,又有四箱计划押给大银行家叶景葵[15],计一百二十多种、四百多册,以罕见本、精本书居多。
他在日记中写的估价是“约可得八千余”,发誓“当于最短期内,设法赎回!”但是最后叶氏的估价才二千元。《劫中得书记》说:“先所质于某氏许之精刊善本百二十余种,复催赎甚力。计子母须三千余金。”[16]
也就是说,叶景葵只给郑振铎不到四个月的资金周转期,就催促他尽快赎回抵押古籍,而且还产生了利息一千一百元,最后“子母”(本金加上利息)三千一百元。
1933年1月,郑振铎就曾向叶景葵抵押书籍借得两千元,“周息壹分”,年底时支付了利息款两百元[17]。

1939年的这次借款,叶氏却催促得紧,可能是因为他当时也在谋划着跟郑振铎一样的古籍抢救工程——因鉴于古籍沦亡,“及今罗搜于劫后,方得保存于将来”,此年5月,叶景葵与张元济、陈陶遗发起筹设上海合众图书馆,叶氏自捐财产二十万作为经费,藏书亦捐入馆中[18]。
“平贾”成群抢购,抬高了书价,郑振铎越来越追不上涨价的速度。8月16日记说: “借洋六十元。连同余下之四十元,存入银行,因明天有中国书店之支票一百元,须来兑现也。此款为购买明版《英烈传》[19]者,明刊小说最罕见,故不惜重值购入。然囊中所余不过十元而已,此十元尚须维持家用若干日,不知如何过日子!好书之癖,终于不改,只用自苦耳。”
但是那天下午,他又去中国书店,买书二册,花去三元。8月19日,身上只有一元几角了,第二天为经济问题,妻子与之吵架。日记中说,“对于书的笃好,终于使精神受了无穷尽的苦闷。”
8月22日,郑振铎取得七月份薪水一百余元,不到数天便将用完。9月2日刚把多年苦心搜访的戏曲珍藏卖给北平图书馆,一拿到款项即去叶景葵处赎回抵押的四箱书,售书所得七千元,才三天时间就只剩下数元了。

他在日记中写道——
在“古书”中搬弄,大似猢狲弄棒,且似染上些市估气息,大可自笑,亦自哀也。
毫无节制地购书,引起了家庭矛盾。
郑振铎1928年出版的《家庭的故事》收入一对姊妹篇《风波》和《书之幸运》,故事是连贯的,写一个名叫“仲清”的知识分子家庭的矛盾纠纷。仲清之妻宛眉染上了打牌的癖好,而仲清嗜书如命。仲清对妻子沉溺于打牌十分不满,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,妻子对他还不断地节衣省食甚至借贷购买古书也抱怨不休,两口子时常发生冲突,二人相互约束——
“你少买书,我就少打牌。”
“你不打牌,我也就不买书。”
他们俩常常的这样牵制的互约着,却终于大家都常常的破约,没有遵守着。[20]
郑尔康(郑振铎之子)后来说,仲清和宛眉的人物原型,正是郑振铎本人和他的妻子高君箴,“当作者在写这两个短篇时,与小说中雷同的情节,正在他的家庭中交替发生着呢”[21]。

与大多数上海的中产阶级主妇一样,高君箴酷爱雀战,“在麻将桌前一坐一个通宵也是常事”,郑振铎1939年、1943年的两种日记里,“箴”或者在娘家高宅,或者在张宅及自己家,组牌局“雀战”至深夜。妻子对于“雀戏”的沉溺,正如郑振铎对于买书的沉溺,何尝不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。
然而1939年郑振铎的借钱买书,还是引致了夫妻间的多场争吵。9月5日记:“今日又与箴诟谇,痛苦之至!完全不能了解我的工作性质与兴趣所在。做一个庸碌无脑筋的人,在家庭里一定幸福得多。”
9月中旬,郑振铎向中国书店出售了二批古书,第一批获款一千五百元。他计划再售去几批书,筹集万元以备缓急之用。

从9月至11月中旬的不到三个月时间,郑振铎共购入一百一十种古籍,耗费近三千余元,深感有心无力:“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,得此千百种书,诚亦艰苦备尝矣。”[22]
注释:
[1] 郑振铎《在腐烂着的人们》,《华美》周刊第1卷第49期,1939年1月。
[2] 胡德华《复社与胡仲持》,《上海“孤岛”文学回忆录》上册,第62页。
[3] 《风涛》是郑振铎写明朝东林党人与魏忠贤斗争的短篇历史小说,刊载于1939年7月世界书局出版的《大时代文艺丛书》之六《十人集》,列在第一篇。
[4] 郑振铎《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,《文学集林》第1辑,1939年,第53—134页。
[5] 郑振铎《劫中得书记》,《文学集林》第2辑,1939年,第39—105页。
[6] 姜德明《徐调孚与“文学集林”丛刊》,《丛刊识小》,南京: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3年,第18页。
[7] 《大公报(香港版)》1939年12月30日,第3版。《申报》1939年12月30日第8版亦有同条报道。
[8] 《华成印刷所主被绑案》,《申报》1940年1月7日,第3版。
[9] 许觉民《孤岛前后期上海书界散记》,《收获》第6期,1999年,第135页。
[10] 郑振铎《劫中得书记》,《西谛书话》,第233—234页。
[11] 同上书,第226页。
[12]同上书,第209页。
[13] 郑振铎《求书日录》,《西谛书话》,第410页。
[14] 1945年郑振铎《求书日录》记:“虽然他已于数年前归道山,但他的所藏至今还完好不缺。”谢光甫藏书在其卒后十年(1949年)散出,多被上海的旧书店拍卖,现上海图书馆、上海师大均有其过藏之书。
[15] 叶景葵(1874—1949),字揆初(一作葵初),光绪二十九年进士,浙江兴业银行、汉冶萍铁厂、中兴煤矿公司等实业的创办人,也是大藏书家。
[16] 郑振铎《〈劫中得书记〉序》,《西谛书话》,第209页。
[17] 柳和城《郑振铎写的两件借据》,《百年书人书楼随笔》,杭州:浙江教育出版社,2017年,第190—192页。
[18] 《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》:“抗战以来,全国图书馆或呈停顿,或已分散,或罹劫灰。私家藏书亦多流亡,而日、美等国乘其时会,力事搜罗,致数千年固有之文化,坐视其流散,岂不太可惜哉!本馆创办于此时,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。”《叶景葵年谱长编》,柳和城编著,上海: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,2017年,第935页。
[19] 万历版《皇明英烈传》,原为沈氏粹芬阁藏书。
[20] 郑振铎《书之幸运》,《郑振铎全集》第1卷,第23页。
[21] 郑尔康《郑振铎》,北京: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,2008年,第107页。
[22] 郑振铎《〈劫中得书记〉序》,《西谛书话》,第210页。
宝利配资-配资排名-配资炒股之家-炒股配资之家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网上炒股配资开户使该事故的死亡人数升至2人
- 下一篇:没有了